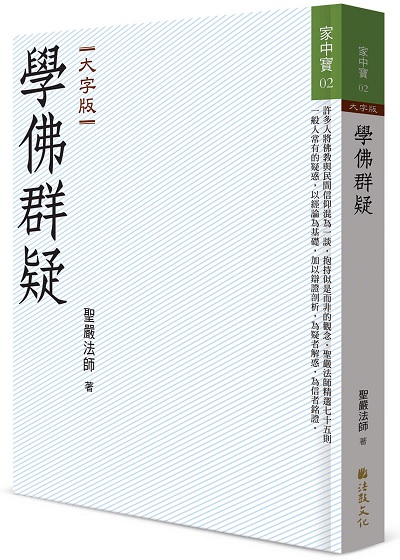內容簡介
生命路徑總在不期然之處轉彎
彷彿為了讓我們看見更廣闊的風景
得獎紀錄
.中山文藝創作獎
.行政院圖書金鼎獎
面對人生中的高山深壑,法師以佛法為地圖來安頓身心,進而將對佛法的踐行領悟,透過義理分明的文字,為我們描繪出生命智慧的藏寶圖。
「我把日記比喻作雪地的腳印,當我記錄的時候,非常地深刻而鮮明,那是我人生的經歷和生命的過程。過了之後,往往又覺得並不重要。就像人在雪地行走時,一步一腳印,步步分明,走過之後不久,腳印便被繼續飄落的雪花淹沒;到了融雪之後,腳印也不會存在。
因為在漫天風雪的景況下,在野外留下的腳印,注意到它的人,恐怕不多;但是在大風雪中還能在野外向前邁進的人,絕不是要讓人家知道自己在雪地上留下的腳印,只要自己知道,為了既定的目標,必須冒雪趕路。」
「我發願,要用現代人的語言和觀點,介紹被大家遺忘了的佛教真義,讓我們重溫釋迦牟尼遊化人間時代的濟世本懷。就這樣,我便勤讀世間群書,尤其專攻佛典,不斷地讀書,也不斷地寫作。」——聖嚴法師
目錄
自序
童年和少年
一、無憂的童年
二、無憾的少年
軍中的歲月
一、我還是和尚
二、從戎不投筆
三、學佛與佛學
出家與回家
一、我真的出了家
二、編輯和寫作
三、求戒的紀錄
戒律與阿含
一、戒律學並不難
二、適合時代的戒律
三、《阿含經》是佛法的基礎
宗教與歷史
一、宗教戰爭
二、我寫基督教
三、宗教比較
四、世界佛教通史
留學生涯
一、趕上了留學風潮
二、初到東京
三、碩士論文
日本佛教的面面觀
一、佛教的宗教活動
二、不務正業的寫作目的
三、日本佛教的學術會議
我的博士論文
一、學術與信仰
二、資料蒐集的困難
三、撰寫論文的發現
東方和西方
一、完成了博士論文
二、我成了海外學人
三、現實讓我改了行
四、禪師.學者.教育家
遊歷和寫作
一、雪地留腳印
二、闊別三十九年的故鄉
三、我的西遊記
四、我是開鑛工人
站在路口看街景
一、沒有目標的目標
二、我的身分只有一個
三、我的中心思想
附錄 拿到博士的那一天
精采書摘
編輯和寫作
我從軍中退伍,正式拿到的退役令,是從一九六○年元月一日生效,而我再度出家披剃改裝的日期,則選在一九五九年農曆十二月初一日。因為我是因病而從軍中徵退,所以打算重回僧團之後,能好好休養身心。一方面藉以懺悔軍中十年來的恣意和放逸,同時抖落一身軍旅生涯的風塵,也希望鑽進東初老人所蒐集的佛教藏書堆中,飽餐一頓。
東初老人為了用文字達成宣揚佛法的目的,繼承太虛大師的遺志,鼓吹「人生佛教」的建立,所以從一九四九年五月,便集合了幾位志同道合的佛教青年,發行了一份月刊,就叫作《人生》,前後經過十多位主編的耕耘。當我投到東初老人座下之時,正好當時的《人生》主編提出了請辭的要求,我也就順理成章地,由該刊作者的身分,一變而成了它的主編。直到我往臺灣南部山中禁足為止,前後為它服務了兩年。
在這段時日之中,我的身體健康,始終沒有好過,經過氣虛無力、頭昏、氣悶、手軟、腳冷、食欲不振、腸胃失控。很多人說,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成道之前,就遇到種種的魔障,我這一點小毛小病算不了什麼!好在有一位前輩的長老,介紹了一位漢醫給我診斷之後,開了兩付藥膏,繼續服用了半年,身體才算從奄奄一息之中漸漸好轉過來。
但是,那一個階段,佛教界能夠為《人生》月刊提供稿件的不多,而且沒有稿酬,開發稿源相當困難,我真佩服前任的幾位主編,真是神通廣大,竟然能夠每月按期出版。因此我向東初老人請教箇中祕訣,他的回答是:「有什麼祕訣啊!沒有人寫自己動手。每天只要寫一篇,一個月就有三十篇了,然後,每篇都給它一個作者的筆名就成了。佛法那麼深廣,人間的問題是那麼地繁複,每天從所聽、所聞、所讀、所觸、所思之中,有寫不完的文章,大好的題材,俯拾即是!」
因此,我就向他請求供稿,他的回答更妙:「不會寫文章的人來編《人生》,我沒有辦法,只好寫嘍!如今你是很會寫作的人,而且我也老了,當然是你自己來寫。」
就這樣,從社論到編後記,我只好埋頭苦幹了。幸而,還有兩位長期供稿的居士,為我們的《人生》消化了若干的篇幅。他們的文章,雖然都是長篇大論,充滿了思想學問,也頗深入,但對於一般的讀者大概都略顯深澀。好在每期出版的數量不多,只有一千份上下,而且總有一、兩篇富有可讀性的文章。特別是偶爾由東初老人口述,而我筆錄成文的社論,經常是「擲地有聲」之作。
我為《人生》向各處邀稿、徵稿、求稿,佛教內外的幾家刊物也向我逼債,這使我除了為《人生》編校和撰稿,也得應酬外邊向我索稿的壓力,在健康狀況如此衰弱的情形下,實在感到寫文章是一樁大苦事。尤其,我編的這一份刊物,它的編輯部、發行部和財務部的辦公室,都在我的斗室裡。工作人員除了我還是我,常常為了版面的調整、新聞的穿插,乃至於一、兩個字的更正,必須親自從老北投火車站到萬華的一個矮小局促的印刷廠,跟排字工人打交道。雖然他們對我的態度都很好,可是每次出版,總要往印刷廠跑上五、六次,也就不是什麼好玩的事了。而據我所知,當時不管是佛教內或佛教外的文化界,大多數是在如此的情況下,把書刊一本本地出版了,送到讀者手上的。可見,文化工作的從業人員,應該具備如此的奉獻精神。
在那段時間裡,我也設法多讀一些大部頭的經論,利用編寫工作之餘,害病求醫之暇,讀完了一部八十卷的《華嚴經》、四十卷的《大般涅槃經》,一百卷的《大智度論》則只看了二十多卷,同時除了早晚課誦及禪坐之外,我還每天禮拜一炷香的「大悲懺」。使得病弱的身心安住在信、解、行的三個原則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