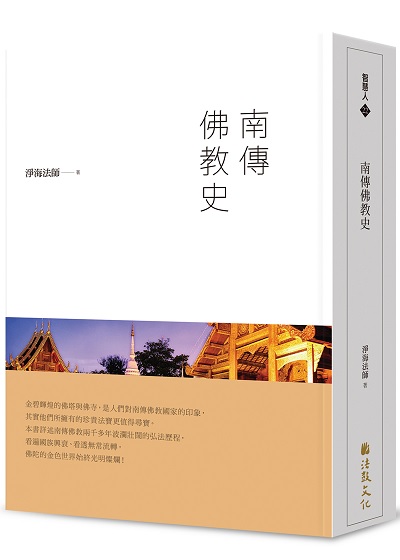內容簡介
禪學真義不辯不明,
禪宗的歷史懸案,
何者為真?何者為假?
東初老和尚以真修實學,幫我們破解禪學迷思!
禪的吸引力,從古至今,從東方到西方,始終不墜。誤解禪學的人,卻可能比了解禪學的人更多。許多人不但將禪學當古董、當哲學鑽研考據,忽略心性問題,甚至質疑《六祖壇經》是偽經,懷疑六祖惠能傳法真實性,種種說法動搖人心,產生信仰危機。有鑒於此,東初老和尚執筆力陳禪學真義所在:「不談修證,不講『明心見性』,還有什麼禪學可說?」
本書直探禪學真義核心,內容分為四大單元:一、叢林制度與禪宗教育,二、論禪學之真義,三、再論禪學之真義,四、關於《六祖壇經》真偽問題。從禪宗的歷史發展溯源,探究叢林制度與僧教育未來,肯定禪是東方文化的精粹。並針對胡適提出的《六祖壇經》是神會禪師所作的論說,提出條理分明的反駁,指出《六祖壇經》只有版本與見性問題,不應有真偽與思想問題。這些文章在發表當年不僅是真知灼見,在現在時空也深具啟發性、撼動力。
作者簡介
東初老和尚
1907年,出生於江蘇泰縣曲塘鎮。十三歲時,由泰縣姜堰鎮觀音庵的靜禪老和尚披剃出家,誦習教法。自幼勤讀強記,自律甚嚴,又寫得一手好文章,智慧超邁,對於經史百家之學也頗多涉獵,許為弘揚佛法的龍象。
1928年,到鎮江竹林寺的佛學院求學;1929年,到寶華山隆昌寺,受具足戒。隨即又到福建廈門,進入太虛大師所創辦的閩南佛學院繼續深造,先後期的同學有印順、竺摩、戒德、默如、慈航、雨曇、覺民等法師,都是一時的俊秀。孺慕在當時佛教界的最高學府中,對日後的治學和研究工作,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東初老和尚是太虛大師的學生,在擔任鎮江焦山定慧寺監院及方丈期間,創辦了佛學院及佛學期刊。1949年來臺之後,創辦了《人生》雜誌;1955年,倡導影印《大正新脩大藏經》,社會各界政要賢達百餘人發起響應,重興佛教文化;1965年,又創辦了《佛教文化》季刊;1967年,中華學術院聘請為該院佛學研究所顧問,從此少問外務,專事佛教著作。晚年,老和尚深感護教弘法必須以歷史為基礎,盡力精心完成了《中日佛教交通史》、《中印佛教交通史》、《中國佛教近代史》三部鉅著。
他的一生對佛教的文化教育,抱有深切的使命感,以及崇高的宗教情操,於此可見一斑。
目錄
自序
叢林制度與禪宗教育——在佛光山東方佛教學院
一、院名釋義
二、佛教中國化的起源
三、禪宗幾位大教育家
四、叢林制度的規範
五、禪宗根本的精神
六、《百丈清規》簡述
七、今後僧教育的前途
論禪學之真義——兼論胡適博士「禪宗史的一個新看法」
再論禪學之真義
一、禪學不是宗教
二、禪學不是訴諸理論的哲學
三、《壇經》只有版本問題,不應有真偽問題
四、《壇經》只有見性問題,不應有思想問題
五、神會與六祖的思想
六、永恆的人格精神
關於《六祖壇經》真偽問題
一、〈法寶壇經略序〉
二、《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三、《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
四、《神會語錄》與《壇經》思想問題
精采書摘
《壇經》只有見性問題,不應有思想問題
「明心見性」,是禪學根本的立場。如何才能「見性」?那必要經過參透思想,體驗事實的工夫。宗祖說:「要大死一番,身心脫落,頓悟自心,本來是佛。」否則,永不能觸及到此種境界真實處。因為,禪是第一義諦,是佛陀自覺心境,達摩稱之為「教外別傳」,或曰「聲前一句」,非是言語所能表示。《楞伽經》曰:「第一義者,聖者自覺所得,非言說妄想覺境界。」是故言說,不能顯示第一義。
達摩西來中土,見此方學人,多未得法,唯以名相為解,事相為行,故不涉名言,不假修證,唯重「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故特以「見性」一語,開創了禪宗。神秀與惠能競選傳法書偈,其關鍵,即在見性與否。一個是七百人的上座,又是位教育家;一個是目不識丁的樵夫,又是白衣。照常識來說,無論如何,惠能不是他的對手,可是問題就出在這一方面。因為神秀立於修證的漸位,以言說為主,陷於「菩提」、「明鏡」一切相對的概念。而惠能頓悟自心,立足於頓悟,以見性為主,否絕一切相對的知識,抽象的概念。因此,不獨要打破「明鏡」,否認「菩提」,並且積極地揮出「無一物」的慧劍,直向被情識知解所縛的神秀胸膛猛刺,把千聖不傳「聲前一句」的消息透露出來,於是獲得六代祖師的榮冠。五祖為他講《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惠能大師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遂啟祖曰:「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祖知悟本性,故付以衣法,許為第六代祖。
由於頓悟自心,始有此妙悟的說法,否則,絕不能如排山倒海一般流露出頓悟自心內在活生命。也就是五祖寧可將大法付給一字不識的樵夫,而不付給善於說法的七百人教授的道理。
由此得知,「見性」為禪宗的內生活的要諦,無論何種場合,或何種時代,都不離開此一內生活立場,否則,就失去禪學的意義。要是丟開「見性」,而以妄心說法,儘管說得天花亂墜,或利用多種語言文字,來表揚禪學的內涵,那只是一種文字禪、口頭禪,宗祖斥之為「野狐禪」,而非祖師禪,更非如來上上禪。因為禪的真相,不容有閒言語,是絕思絕慮的根本法。所以古德開示門人,總要離開言說,顯示禪的第一義。試舉《碧巖錄》第七十三則,提示禪的根本法:僧問馬大師:「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某甲西來意。」馬師云:「我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問取智藏去!」師著語云錯。僧問智藏,藏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為汝說,問取海兄去!」僧問海,海云:「我到這裡卻不會。」僧舉似馬大師,馬師云:「藏頭白,海頭黑。」
馬祖道一嗣南嶽懷讓禪師法,住江西,法人滿天下,也就是西天二十七祖預示的「馬駒踏殺天下人」的人物。「西來意」,是禪宗最重要的公案,其開端始於馬祖。這個問意,來自達摩大師答梁武帝的「廓然無聖」。因為「廓然無聖」,不但否絕一切相對的知識,抽象的概念,更把世間一切議論、開示、說法都否絕掉,而顯出超凡入聖自證自悟真境界。然而,達摩西來究竟帶來些什麼?就請馬大師指示。既曰「離四句,絕百非」,是無言無說。在無言無說當中又從何說起呢?於是所得的答語:一個推「勞倦」,一個推「頭痛」,一個推「不會」,把「西來意」愈推愈莫名其妙,致後來祖師關於「西來意」問答,無慮數百次反覆的商量,也就是種因在此。要從理論上說明「西來意」,畢竟是不可能的,何況又是「離四句,絕百非」,又從哪兒說明祖師「西來意」?可是從「勞倦」、「頭痛」、「不會」上,卻把祖師「西來意」赤裸裸地完全顯露出來。
因為禪的根本法,是法住法位,有佛不增,無佛不減,永恆地存在著,是離開言說相,是絕思絕慮活動在吾人眼前。等於問道,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答曰:「柳綠花紅。」因為一切法,法住法位,又如何道出「柳是綠」、「花是紅」的本來面目呢?因此,馬大師說:「藏頭白,海頭黑。」無異說:鷺是白的,鳥是黑的,青是青的,紅是紅的,不用理論分別「離四句,絕百非」的言詮,只以「藏頭白,海頭黑」,顯出會與不會自證內生命,絕對的本來面目,冷暖自知的「祖師意」。是故禪的根本法,非是妄心言說所顯之境。
百丈懷海禪師,嗣馬祖法,住百丈大雄山。百丈開示學人,也採用馬祖:「離四句,絕百非,如何說禪?」百丈一日問侍者溈山:「併卻咽喉唇吻,作麼生道?」山云:「卻請和尚道。」丈云:「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碧巖錄》第七十則)
這個問意,很明顯的,這與「離四句,絕百非,如何說禪?」其意義相同。百丈問溈山:「閉卻咽喉唇吻如何說禪?」禪,既屬絕思絕慮,言語道斷,而百丈卻要溈山超出言語思路道出禪的真實相,哪知溈山卻用逆襲的方法:「若依語言可以道出禪的真面目,那麼,就請和尚道罷!我是沒有辦法的。」這實出乎百丈意外的襲擊!但百丈也很坦然的道:「我向汝道未嘗不可,可是一說出來,將來恐怕要絕了嗣我法的子孫。」這等於說,要以言語指示給人,那便是一種學說,是一種妄想,不是教外別傳。別傳之法,是直覺的妙悟,是絕思絕慮的根本法。若依言語相傳,不但落於知見,並要斷絕眾生的慧命。由此得知,五祖之所以未將大法傳給神秀,六祖之所以要訶斥神會,其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他兩人未能「見性」。所以禪不在言說之間,而重在「見性」。